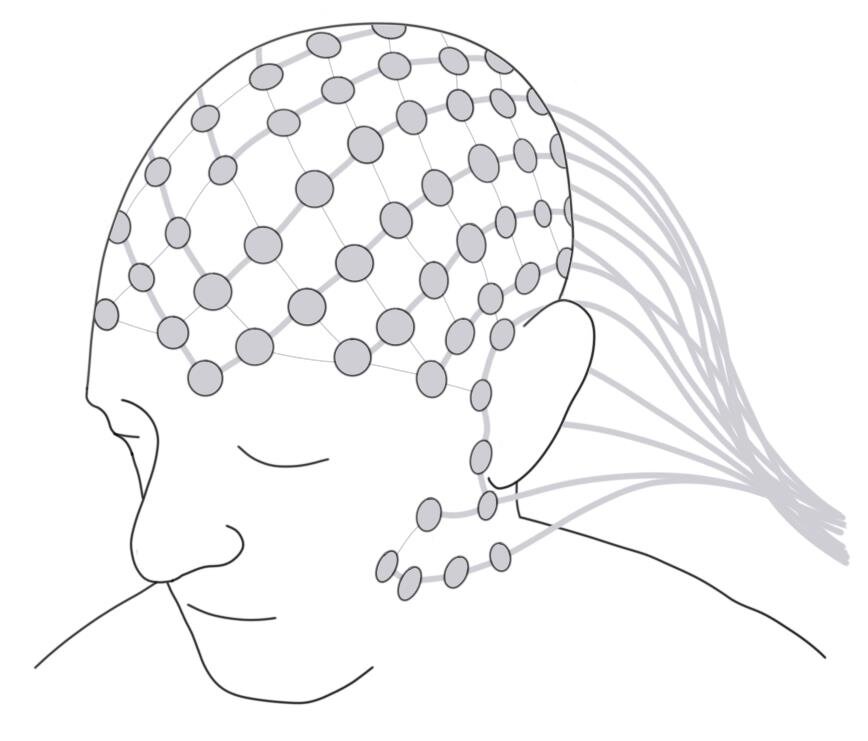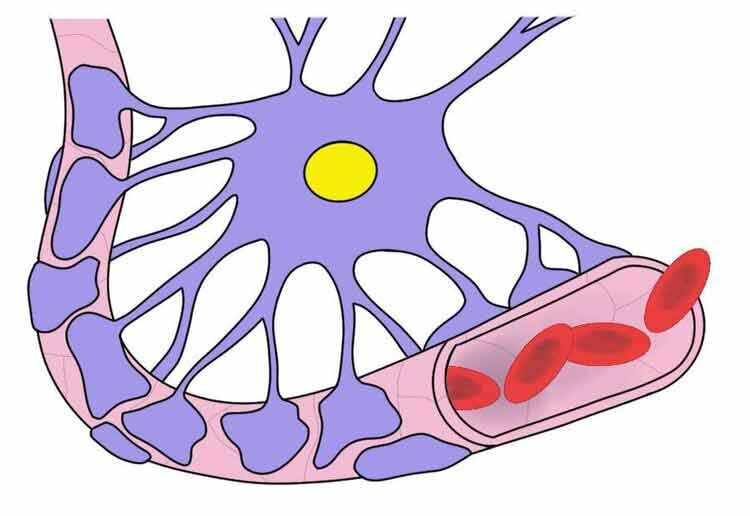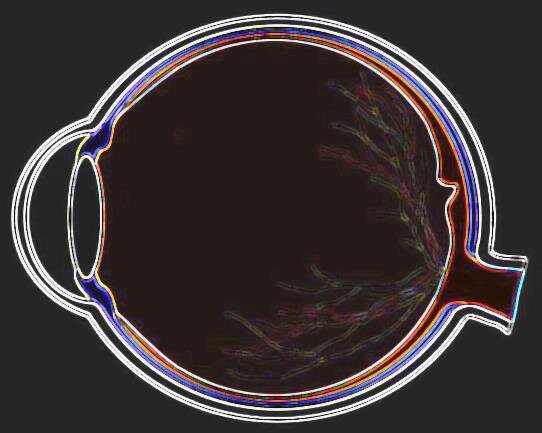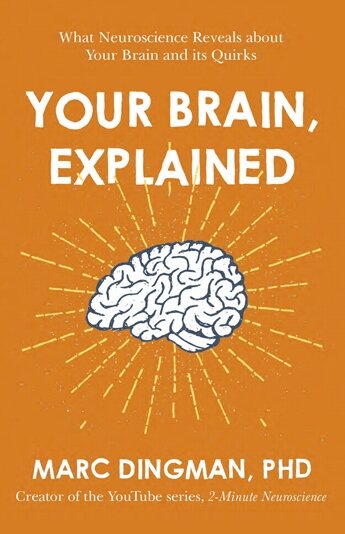搜索文章和视频在这里(为定义,使用术语表):
神经科学两分钟视频
通过简单易懂的2分钟视频学习神经科学的基础知识。
了解你的大脑文章
通过这些简短的参考文章可以更好地了解你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。
其他文章
扩展你的神经科学知识与这一系列神经科学文章,在广泛的主题。
最近的内容
术语表
定义了超过500个神经科学术语,还有补充图像、视频和相关内容的链接。
你的大脑,解释
(封底):睡眠。内存。快乐。恐惧。语言。我们每天都在经历这些事情,但我们的大脑是如何创造它们的呢?你的大脑,解释是围绕你的大脑灰质的私人旅行。基于神经学家马克·丁曼在YouTube上的热门系列,两分钟神经科学这本书用真实生活中的例子和丁曼自己手绘的插图,友好而引人入胜地介绍了人类的大脑及其怪癖。
表扬你的大脑,解释:
《Your Brain, Explained》将神经学史上的经典案例与探索大脑秘密的最新技术成果相结合,读起来就像侦探小说集。~Stanley Finger,博士,华盛顿大学(圣路易斯)心理与脑科学名誉教授,《神经科学起源》作者
“这是一本内容丰富、通俗易懂、引人入胜的书,适合任何对大脑如何工作哪怕是最轻微的兴趣,但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的人。”~Dean Burnett博士,《快乐的大脑和白痴的大脑》的作者
丁曼将经典研究与现代研究结合起来,编入易于理解的章节,为快速发展的神经科学领域提供了一本优秀的入门读物。~Moheb Costandi,作者,《神经可塑性和你真正需要知道的50个人类大脑想法
“…高度可读和可访问的介绍,大脑的操作和神经科学的当前问题…这是对这一领域的精彩介绍。”~Frank Amthor,博士,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心理学教授,《傻瓜神经科学》作者
这是一本有趣且信息量大的书……我学到了很多,你也会的!”~约翰·e·道林博士,哈佛大学戈登和卢拉·冈德神经科学研究教授,《理解大脑:从细胞到行为到认知》一书作者